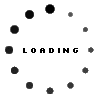Foreword
如果說建築是人與生活的連結,宗教建築則是同時連結人與神性、人與人心的橋梁。
當代的宗教建築已經不僅只追求宗教的功能性,更多時候展現的是建築師對於心靈力量和神性的探究,同時,更是在地生活、聚落經濟的縮影。從世界到台灣,透過現代宗教建築巡禮,從不同的視角與高度,閱讀不同地域的文化與歷史。
在全球化與世俗化浪潮下,宗教建築的樣貌不再只是過往莊嚴華麗的回聲,而是更接近一種「靜默的凝視」──用空間、光影、材料與人的關係,重新界定信仰在當代生活中的意義。以下全球各地5座當代宗教建築,來自亞洲、歐洲與中東,它們或簡約、或象徵,皆不約而同地回應了當代社會的精神渴望,也展現出建築師對信仰與空間之間微妙關係的深刻詮釋。
南非|Bosjes南非小教堂
飄浮的祈禱,曲線之詩與詩篇之光
完工時間:2016年
建築設計:Steyn Studio
在南非西開普省布里德谷的葡萄園與山巒之間,一座彷彿懸浮於天地之間的教堂靜靜展開它的弧線詩篇。這便是Bosjes南非小教堂(Bosjes Chapel)──由倫敦建築工作室Steyn Studio所設計,以其優雅飄逸的白色屋頂,在建築界與信仰空間中掀起一場柔性的革命。
教堂建築坐落於一方抬升平臺,前方鋪設反射水池,倒映屋頂起伏的波形,如湖上漣漪,亦如展翼欲飛的鳥。這飄浮感不只是視覺設計,更是一段信仰語言的詮釋──靈感取自《詩篇》36:7:「人的子民在你翼下可以投靠。」屋頂造型亦向西開普傳統荷蘭殖民建築(Cape Dutch)特有的折線山牆(Holbol Gable)致意,同時呼應遠方連綿山脈的剪影。

↑南非小教堂以起伏白色屋頂回應《詩篇》與西開普山巒意象,倒映於水池如展翼欲飛,信仰與自然融為一體。
這一座非特定宗派的現代禮拜堂,刻意淡化傳統宗教符號,而是以建築本體承載靈性意涵。內部為單一矩形禮拜廳,無講壇與雕飾,僅以廣角玻璃引山谷、葡萄園、石榴林入室,模糊建築與大地的邊界。地面採用高拋水磨石材質,宛如鏡面,映照著屋頂線條與光影交錯。牆面潔白無飾,光線自側窗與玻璃祭壇灑入,將室內空間化為一處純粹的沉思場域。十字架懸浮於透明玻璃之上,與遠山背景合為一體,彷彿將祈禱投向整個大地。
這座建築的結構背後,也是一場技術與工藝的挑戰:設計團隊採用 3D 建模與預製木模板搭建支撐,再以混凝土手工灌漿成型,每一道曲面皆需人工彎曲鋼筋支撐,最終達成這片如絲綢般柔韌卻堅實的屋頂,不以高度或宏偉取勝,而是以靜默與純粹回應人們對當代靈性空間的渴望。

↑Bosjes教堂無講壇與雕飾,大片玻璃引入山谷與葡萄園,水磨石地坪映出天光與曲線屋頂,祈禱彷彿輕觸整片大地。
土耳其|薩其林清真寺
地下的光,讓禮拜回到本質
完工時間:2009年
設計者:Zeynep Fadıllıoğlu主導設計,Hüsrev Tayla擔任建築顧問
傳統清真寺的尖塔與圓頂構成了歷史的天際線,而位於土耳其伊斯坦堡於斯屈達爾區(Üsküdar)的薩其林清真寺(Şakirin Mosque),則以截然不同的姿態悄然現身。這座2009年落成的清真寺,最為人矚目的,不僅是它現代化的輪廓,而是由女性設計師Zeynep Fadıllıoğlu領軍之事務所主導完成,開創伊斯蘭世界前所未有的紀錄。
薩其林清真寺圓頂採用鋁合金建材,牆面結合石材與玻璃,禮拜大廳以淺灰與銀白調主色,沒有繁複圖騰,也不強調歷史復刻,而是讓光與空間自成一種神性語彙。來自穹頂的光線,如水波般灑落,照亮信徒席地而坐的祈禱毯,亦映照出一種屬於當代的靜謐與尊嚴。

↑薩其林清真寺沒有繁複圖騰,也不強調歷史復刻,以鋁合金圓頂與石材玻璃牆面構成現代禮拜空間。
Zeynep Fadıllıoğlu認為:「神聖空間應是包容的,不只為信仰,更為所有尋求安定的人而存在。」她以纖細的光線處理、懸浮吊燈與水晶書法為空間注入柔性,也讓這座清真寺跨越宗教、性別與時代的藩籬。即使是非穆斯林,也能在其中感受到一種關於光、安靜與人的共同語言。

↑來自穹頂的光線,如水波般灑落,照亮信徒席地而坐的祈禱毯,亦映照出一種屬於當代的靜謐與尊嚴。
瑞士|聖若翰洗者教堂
石砌之心,光落山谷的精神地標
完工時間:1996年
設計者:Mario Botta
1986年,一場突如其來的雪崩摧毀了瑞士南部莫格諾(Mogno)小村莊中的老教堂與十多間房舍。所幸當時無人受傷。數年後,著名建築師Mario Botta受邀在原址重建這座獻給洗者若翰的教堂(Chiesa San Giovanni Battista)。
與其說這是一座重建,更像是一場信仰與地景的再定義。教堂建築為圓筒狀,覆以玻璃斜頂,輪廓簡潔卻力道十足。波塔選用來自瑞士南部阿爾卑斯山脈中佩恰鎮的白色大理石與當地深色花崗岩,以深淺交錯的方式鋪陳外牆與室內牆面,形塑出如地層般的時間感,也喚起人們對災難與重生的記憶。

↑聖若翰洗者教堂以圓筒建築、玻璃斜頂與深淺相間的石材,象徵地層與記憶,訴說信仰在災後重生中的靜默力量。
教堂內部僅能容納15人,無窗設計使自然光從屋頂灑下,成為唯一的光源。光線自玻璃屋頂漫入,投影在黑白相間的石牆上,營造出神聖、寧靜、幾近冥想的氛圍。空間極簡,座椅、講壇、十字架皆內嵌於建築本體,讓使用者不被干擾地沈浸其中。
聖若翰洗者教堂並非傳統意義上的華美建築,它曾因造型激進與當地傳統衝突而引起爭議。但時至今日,它已成為瑞士當代建築的經典,證明宗教建築亦能突破形式限制,在災後重建的基礎上,為信仰與空間之間創造出全新的語言。

↑教堂內部僅容15人,天光自玻璃斜頂灑落無窗空間,映照黑白石牆。極簡設計內嵌座椅與講壇,創造出全新印象的信仰靜域。
芬蘭|康比禮拜堂
城市中的靜默,木質橢圓中的光與靜
完工時間:2012年
設計者:K2S Architects
芬蘭赫爾辛基的康比禮拜堂(Kamppi Chapel of Silence)矗立於商場與交通樞紐交會的市中心廣場,如同一顆巨大的木質種子。橢圓形建築體以芬蘭雲杉板包覆,溫潤細膩的質感形成一種視覺與心靈的緩衝。走近它,就像走入一段安靜對話的開端。
這座僅11公尺高的小禮拜堂,結構上由膠合層板打造主體骨架,展現出高度的木構工程技術。建築師採用精密切割工法製作曲面構件,再由現場人工組裝,層層堆疊出橢圓體的柔和弧度。外牆選用加壓處理過的芬蘭雲杉,經過多道表面塗層,呈現出自然油亮質感,並可抵抗極地氣候的乾溼變化。

↑康比禮拜堂外牆以雲杉木板層層堆疊,構築11公尺高橢圓曲面,展現精細木構技藝與北歐式安寧氛圍。
內部無宗教符號、不舉行儀式,卻擁有無盡的寂靜與包容。牆面以北歐白樺木條拼貼,沿曲面溫潤包覆,每道弧形皆精準對位,構成聲音柔化的天然音箱。聲音進入後不反彈、不喧嘩,只在木壁間輕輕消融。天花板則藏入環形光帶,採用間接照明設計,讓自然或人工光線以最柔和方式瀰漫空間,無一刺眼。人在其中,不是被教導信仰,而是被允許靜聽自己。
這座由赫爾辛基市政府與教會合作打造的建築,屬於公共空間與靈性照護的交會點。它不強調宗派,而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尊重與傾聽,在北歐式的克制與人文關懷中,重新定義信仰空間的社會功能。對日益孤獨的現代都市人而言,康比禮拜堂提供了一種安靜而無條件的陪伴,是屬於每一個人的靈性避風港。

↑禮拜堂內部以白樺木弧形包覆、隱藏光源營造柔光,內部無宗教符號、不舉行儀式,是屬於每一個人的靈性避風港。
日本|光之教堂
一束光,劃開信仰與沉思的邊界
完工時間:1989年
設計者:安藤忠雄
1989年完工的光之教堂(目前暫停對外開放),是安藤建築哲學的代表作,也是當代宗教建築的經典。建築位於大阪郊區住宅區內,以清水混凝土鑿成矩形量體,正面開一道十字裂縫,讓自然光貫穿其中,構成整體空間的核心。
教堂是由基督教茨木春日丘教會成員的奉獻捐款而來,內部僅有幾排長椅、粗糙混凝土牆與那道光。當日光穿透十字,直射講壇,形成神聖而極簡的信仰經驗。這不只是形式的戲劇性,而是安藤對「空」與「光」的執著實踐──將信仰從儀式抽離,還原為一種內在覺察。

↑安藤忠雄以留白與限制塑造凝視空間,陽光穿透混凝土,形成信仰、建築與光的對話,引導人們直面內心與永恆。
安藤曾說:「我不設計建築,我設計人們與空間的關係。」光之教堂就是一場關係的建構,它的神聖不是來自建築的裝飾性,而是來自「留白」與「限制」帶來的凝視力量。它是一場關於信仰、建築與光的永恆對話。當陽光與混凝土交會,沉默勝於言語,在那片光中,人們得以直面內心、面對永恆。

↑1989年完工的光之教堂,以清水混凝土鑿成矩形量體,是安藤建築哲學的代表作,也是當代宗教建築的經典。
當代宗教建築不再只是信仰的外在象徵,而是化為一種靜默卻深刻的精神實踐──它們低調、不張揚,卻以空間、材料、光影、比例精準地呼應了人們內在的渴望。
這些建築並非「去宗教化」,而是「再精神化」,將神聖從形式中解放,還給每一個人的體驗與思索。它們不只是建築,更是時代中最溫柔的呼喚,也是一場持續進行中的靈性建築革命。
Text/Y.S
Photo/達志影像/shutterstock
延伸閱讀:
【設計咖啡館】Modern Mode & Modern Mode Café──光影之間的巴黎情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