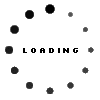Foreword
「群山在召喚,我能不出發嗎?」《尋找台灣特有種旅行》作者邱一新,一路走來都是雜沓城市中的白領上班族,然而他每逢閒暇,便一身輕裝將自己丟進僻靜的山林,走進台灣各地角落,展開另一種旅行。這10餘年來探訪台灣古道山旅紀行所寫成的《徒步旅人》,帶你走在島嶼地圖之外,徒步一條少有人走的路,對於植況地貌、常民風情的描寫,以及引述之山史地誌文字,讀來令人心神嚮往,讓人也想依循腳步,探幽尋訪古道的真實風景,站在島嶼的記憶深處,諦聽腳下的歷史跫音。
學習「如何看見?」:是古道健行,也是心靈漫步
啜飲咖啡後,我在檜山駐在所遺址轉悠,果不其然,找到好幾樣「記憶符號」(亦有稱「垃圾古蹟」),像是日本酒瓶、瓷碗、礙子等碎片。雖然也想找到更多的生活用品,如茶具,甚至彈殼、錢幣,然而毫無所獲。儘管如此,我並沒有停止做白日夢,還是妄想在草叢中踢到什麼遺物,忽見草地上有一只半掩埋在土裡的墨綠色玻璃瓶,便好奇提問:「這是酒瓶嗎?」
山友見狀挖出來,只見瓶身有「NODASHOYU」的字樣。博學的領隊Chris研判是「野田醬油」,即後來與「萬上味醂」合併的「龜甲萬醬油」前身。所以這瓶醬油顯然是1940年龜甲萬商標統一前,從千葉縣野田市工廠運到橫濱,搭船到基隆,再循福巴越嶺道運至此地,光思忖這趟上千公里旅程就不勝唏噓──不禁興起了想像,將人物放進歷史環境中去推演情節,去拼湊昔日駐在所生活情景:駐警如何吃?如何洗澡?如何結婚?是否娶了泰雅「內緣妻」(在本土早有妻室的日警,來台再娶的未登記婚之原民女子)?如何扶養子女?同時,我也想知道他們與泰雅人如何互動?我甚至虛構了一位叫村田的日本警官,從遙遠的九州家鄉來到帝國殖民地,欲有所奮發,參加了「理蕃」戰爭,協力三井財團蕃地拓殖,後奉派到「線外蕃」領域的駐在所,執行「教化」職責,過著耀武揚威又提心吊膽的寂寞日子,只能以酒精麻醉自己,在酒酣耳熱之際高唱〈蕃界警備壯夫之歌〉抒發壓力:
「今日的作業是爆破斷崖,聲響在山谷間迴盪,延續修築橫斷道路,男人的汗水愉快地流著;教化太古之民,是我等尊榮之務,首狩的手飼養著蠶,是可愛的兄弟;強健的男人在蕃山老去,厭倦了辛苦的勤務,可愛的妻子臥病在床,由衷的怨恨群山;7、8歲幼兒,送往市街的學寮,雲深處的幾重深山,早晚都挽著袖子工作;駐守治安防備動亂,仰望著先人的功勞,我願意一死報國,成為深山中芬芳的櫻花。」(摘自金尚德《峽谷山徑二十里》)
從歌詞可知,日治中期以後,理蕃警察的勤務轉為監修道路、教育蕃童、產業指導等,不再是防蕃征戰;但沒唱出來的還有執行「蕃社併合」、「平地誘致」、「集團移住」、「皇民化運動」等瓦解先住民社會的挑戰。而最終皆如櫻花飄落化作春泥,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
可見觸景傷情會將人送到另一個時空點,行走到更遙遠的地方。或借用詹宏志《旅行與讀書》附錄中一句話:「旅行窮盡處,正是幻想啟程之時。」的確,透過閱讀和想像,古道成了時光隧道,因為每一條古道都存在著兩種以上時間。

上述臆想,來自閱讀《遙想當年台灣:生活在先住民社會的一個日本人警察官的紀錄》有感。這是青木說三在昭和3年(1928)派駐台東里壠支廳(今關山)和「內本鹿警備道」(西起六龜、東抵桃源,全長約124.7公里)各駐在所,擔任18年理蕃警官的回憶錄。雖說是從日方「進步史觀」和「帝國秩序」角度寫就,卻是在帝國的架構中尋找台灣的定位。如同之前的清朝、之後的國府,如今都是台灣歷史的一部分,或能給予某種啟發──殖民地人民真的在乎異族統治嗎?還是只在乎日子過得好不好?
對先住民而言,部落意識就是國族意識,迫於無奈接受異族統治並不等於國族認同;反之,帝國主義者的心態,來自種族優越感的偏執心態,面對弱勢文化時往往企圖同化,因此喪失文化交流和文化多樣性的可能性。
順帶一提,內本鹿警備道原本是布農族郡社群領域,東段諸社即在青木說三勸說下遷移至都蘭山西麓,散布於今桃源村和鸞山村,期間還爆發「內本鹿事件」;猶記得20多年前,我偕家人至台東延平鄉「布農部落休閒農場」,那時還覺得奇怪,布農族怎會在淺山區。直到遇見「鸞山森林文化博物館」主人阿力曼,才略知其祖輩遷徙歷史。
但,對不起,這不是本文要說的故事,暫且按下。我想說的是,日治警備道路與族群關係及地理形勢息息相關,一旦完成部落遷徙,警備道路和駐在所也就棄置荒廢。
儘管此書主張日本殖民帶來現代化,但不能否認,一連串血淚斑斑的原民抗日事件、攻擊駐在所、馘首,就是先住民對殖民者的回覆。
真相不知凡幾,到底是日警的真相?高砂族的真相?漢人的真相?抑或後代人推敲的真相?行走在古道的旅人,又可以沉澱出什麼樣的智慧和想像?
大自然中的「明信片風景」,諸如神木、瀑布、溪澗、奇岩異石,幾乎不容易被錯過;但我們往往看不見或忽略了旅途中具有人文價值的遺痕、或具生態意義的景物。所以,我一直在跟各領域的專家學習「如何看見」:如何識見野花草木、如何聆聽蟲鳴鳥叫、如何尋見岩層化石、如何辨識先民遺物遺跡──古道上的小廟、石屋、植樹、清兵營盤、日警駐在所等。
因此,不同於觀光旅遊的消費性質,古道健行意味著一種教育性的行動,也隱然帶著浪漫的情懷。在我看來,這不僅是一場連結過去記憶的奇幻旅程,也是一條追尋智識的道路,冀望開創新的意義上的文化場域,看到新的意義上的旅行風景。請容我再次引用美國文學家亨利・米勒所言:「旅人的目的地從來就不是地方,而是一種看待事情的新方式。」或如他的地下情人,作家阿內絲・尼恩(Anaïs Nin)所寫的:「我們旅行,但有些人永遠在尋找另一種狀態,另一種生命,另一種靈魂」(We travel, some of us forever, to seek other places, other lives, other souls),真是深得我心之言。我的經驗是,旅行到最後,往往是一條向內走的路徑,終將抵達思想的領域,就像人終究要回到命運為他安排的道路上。
如今,在我人生的「甜點」階段,我開始練習一種「心靈漫遊」的旅行方式。就像繆爾有個令人難忘的說法:「你要讓陽光灑在心上,而非身上;溪流穿軀而過,而非從旁流過。」走巴福越嶺道即有此感受。
(本文節錄自《徒步旅人:深入台灣20條故道,在走路與獨處中探索島嶼記憶,與自己對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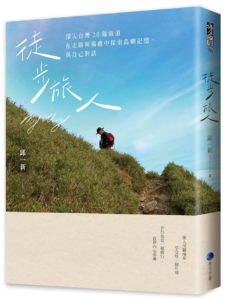
▋《徒步旅人:深入台灣20條故道,在走路與獨處中探索島嶼記憶,與自己對話》
作者:邱一新
出版社:馬可孛羅
Editor/小島與松
Photo/馬可孛羅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