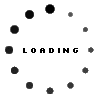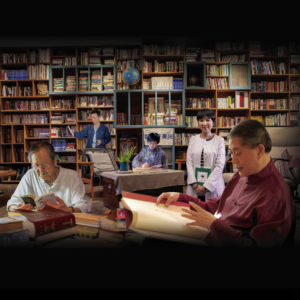Foreword
《萬有自然力》是一部以科學書寫自然之美的作品。牛津教授凱西.威利斯結合生物學與心理學研究,揭開自然對人體的深層影響──從森林氣息到泥土氣味,每一種元素都在修復我們的感官與情緒。書中引導讀者以理性重新理解「自然療癒力」,也以感性提醒人與萬物的共生關係,深入淺出的文字,讓人意識到,療癒並非遠方的風景,而是存在於日常的呼吸、觸覺與光影之中。
多麼令人沮喪的統計數據啊──全球每年有71%的死亡是非傳染性疾病造成的,包括心血管疾病、心臟病發作、中風、氣喘等呼吸系統疾病,以及癌症、糖尿病和精神疾病,而且這個比例還在上升。儘管近幾十年來,麻疹、愛滋病和肺結核等傳染病的死亡率已大幅下降,非傳染性疾病的死亡人數依然以驚人的速度逐年增加。
同樣值得警醒的是,都市化程度的提升,似乎與非傳染性疾病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係,說明兩種情況某種程度上是互相影響的。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根據推測,到2025年將有超過7成的人口生活在都市環境中,而此趨勢仍在逐年增長。非傳染性疾病以及其他與都市環境相關的健康問題,現在已經有了充分的證據支持,甚至形成了一個專門的術語:「病態建築症候群」(sick building syndrome)。這個總稱涵蓋了某些建築環境的特徵,這些特徵會導致在那裡居住或工作的人感到不適,甚至使他們的健康狀況低於應有水準。
我們需要在城市中生活和工作,但它似乎正慢慢扼殺我們。好喔。那我們該怎麼辦呢?多運動、學習放鬆技巧、改善飲食、服用處方藥,這些方法都是經過千錘百鍊的建議──但對死亡率似乎沒有太大幫助。不過,有一項醫囑清單中的建議往往容易被忽視,實際上卻可能帶來深遠的改變,那就是增加與大自然的接觸,不僅在戶外有效,室內也有效。
那麼,能不能把自然帶進室內呢?
室內融入自然,千年前已存在
事實上,千百年來人類不斷嘗試將自然融入室內環境──有時以建材的形式,有時則作為裝飾元素。從古早年代開始,木材便是建築中不可或缺的材料,不僅因為在地取得容易、材質堅固、可塑性又高,能打造出各種形狀和規模的構造。從可容納30人的新石器時代長屋,到只供單一家族居住的小型圓屋,木材都是主要建材。雖然早在西元前7千年左右,近東地區的早期社會就已開始使用磚塊和石材,但考古證據顯示,木材依然在這些建築發展的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這一點直到今天依然沒有改變。
用真正的盆栽和植物畫作來裝飾室內空間的風潮,直到17世紀才真正興起。當時,植物學、園藝,以及描繪植物與其他自然物的靜物畫,成為流行的消遣活動。其中,有一本書尤其激發了人們將盆栽作為裝飾的興趣──那就是休.普拉特爵士(Sir Hugh Plat)於1608年出版的《花卉天堂》(Floraes Paradise)。
當時的休.普拉特,可說是現代「居家與花園」設計師的先驅。他所撰寫的第一本園藝手冊《花卉天堂》,書中有一章名為「門扉之內的花園」(A garden withindoores),專門探討室內園藝,並提出了許多實用建議,例如針對家中特定空間推薦合適的植物品種。凱瑟琳.霍伍德(Catherine Horwood)在她的《盆栽歷史》(Potted History)一書中指出,休.普拉特大力推薦「多花薔薇、月桂樹和血葉蘭」適合放在房間的陰暗角落;也提供讓康乃馨和玫瑰四季盛開的訣竅;並稱讚一種名叫紫景天(orpin)的景天屬植物,具有耐性強、壽命長的優點。
許多植物史學家認為,普拉特的書是將植物帶入家中成為裝飾的一個轉捩點,在此之前,家中擺放植物純粹是為了藥用和烹飪目的,至少在西歐是如此。
從17世紀中葉起,隨著世界探險的腳步踏足更多未知之地,人們開始熱衷在室內展示充滿異國情調、色彩繽紛的熱帶花卉。直到今日,這股風潮依然延續。在喬治亞時代和維多利亞時代,很流行用異國植物來裝飾居家和溫室,這股風潮一直延續到20世紀。「袖珍椰子」(Parlour palms)成為家庭中最重要的裝飾之一,這個統稱涵蓋了來自南美、亞洲與非洲的各種棕櫚、蕨類和其他耐陰植物。但我們愛的不只有實體植物:人們常用靜物畫來裝飾牆壁,自然主題也在新藝術風格(Art Nouveau)的建築師以及像威廉.莫里斯這樣的設計師作品中流行起來,進一步延伸到壁紙設計、家具和織品上──就像我們的祖先曾在木雕壁飾與花格窗上留下的自然印記一樣。
然而,從1950年代末以來,一切悄然改變。我認為客觀來說,在選擇建築材料或室內裝飾的過程中,自然開始逐漸被排除在外。混凝土、石棉、鋼鐵、塑膠和石膏板等材料大行其道,簡約、筆直、講求功能性的設計風格成為主流。天然素材,以及那些帶有自然曲線、形狀和紋理的設計,逐漸消失在居家、學校或辦公室,連盆栽植物都被換成了塑膠製品。當時的社會背景與戰後重建的迫切需求,進一步推動都市設計走向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未來已然降臨──卻是一片灰色。許多人認為,也正是在這個時刻,我們與建築環境的關係開始惡化,而這種斷裂,至今仍在影響著我們的身心健康。
親生命概念帶來的新視野
生物學家愛德華.威爾森在1984年提出「親生命」(biophilia)一詞,用來描述人類天生對大自然的親近感──我們需要與自然為伍,才能真正達到身心健康的狀態。這個觀點廣受認可,彷彿威爾森只是替我們說出了早已感受到、卻尚未能用語言表達的事實。我們之所以需要保護自然、讓自己活在自然之中,不只是為了它能提供的物質利益,也是因為它對我們的心理和身體健康有著深遠的正面影響。「親生命設計」的概念於焉逐漸形成,主張在我們生活與工作的空間中融入自然元素,以強化人與自然的連結,進而提升整體的幸福感。
2015年,史蒂芬.凱勒(Stephen R. Kellert)和伊莉莎白.卡拉貝絲(Elizabeth F. Calabrese)在一篇圖文並茂的論文中,歸納出實現親生命設計的三大主要方式。第一,直接引入自然作為設計的一部分,使其成為空間特色,例如盆栽植物和植生牆。其次,透過間接方式營造自然的感受,例如自然意象的圖像、天然材料與色彩,或模仿自然形態的設計語彙,成為室內外的焦點。第三,讓人即使身在室內,也能接觸到戶外自然,例如透過建築手法,將景觀、聲音、自然光和開放空間融入體驗之中──比方說,在開放式辦公室空間中設置大量窗戶。
但這些室內的自然設計特點,真的對健康有明確的益處嗎?就目前我們的理解,包括嗅覺、視覺、聽覺、觸覺,以及本書其他章節提到的各種與自然相關的微感知,我衷心希望答案是肯定的!
(以上摘自《萬有自然力》,行路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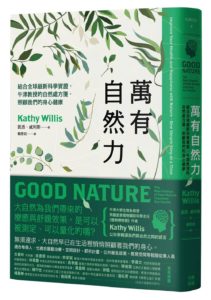
▋《萬有自然力:結合全球最新科學實證,牛津教授的自然處方箋,照顧我們的身心健康》
作者:凱西.威利斯 Kathy Willis
譯者:賴彥如
出版社:行路
Editor/小島與松
Photo/Pexels、行路出版
延伸閱讀: